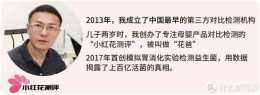□陳侃章
一首《楓橋夜泊》,把“天下楓橋”都聚焦到姑蘇楓橋和寒山寺身上,這就是文學名篇的影響力,是人文因子持續發酵的結果。放眼望去,這種事例並不少見,如蘇東坡在黃州寫《赤壁懷古》,把三國古戰場嘉魚赤壁的風光給吸附了,“黃州赤壁”知名度遠超歷史經緯中的“嘉魚赤壁”。相關方對蘇東坡真是愛恨交織!
那麼,諸暨楓橋又作如何觀呢?諸暨楓橋的歷史長度稍遜於姑蘇楓橋,相對說來是“後起之秀”,然而後起的楓橋以匯聚各方英才的胸懷,快速流淌成一條蔚為壯觀的文化長河。
一、楓橋文脈形成於宋代
作為行政建置的楓橋誕生於北宋末期。對楓橋的來歷,文史專家陳炳榮先生所著《楓橋史志》有考證:此地唐朝屬大部鄉永昌裡,有條楓溪穿過,在楓溪江上建立了一座頗有規模的石拱橋,成為婺越往來的主要通道。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在此設立楓橋鎮,這是楓橋作為行政建置的開始。

楓溪上現存的楓橋夜景。
60多年以後,也即南宋乾道年間,以楓橋鎮為中心,從諸暨分出10個鄉鎮設立了義安縣,不過未滿三年即裁縣復鎮。楓橋建縣雖然短暫,但宋代古縣的歷史還是成立。
兩宋尤其是南宋初期,北方士人大舉南遷。出類拔萃的“楓橋三賢”——王冕、楊維楨、陳洪綬,及趙、何、駱等名門望族的祖上就是在這時期遷入楓橋落籍,一時多少落魄豪傑!

王冕畫像。
王冕的楓橋始祖王琳,南宋時為官諸暨,侄子王文炳在楓橋定居,王氏一族蓬勃發展。
楊維楨的先人在北宋遷徙楓橋,期間出了頗有聲望的名醫楊文修,明清《諸暨縣誌》都有他的傳記。

陳洪綬畫像。
陳洪綬楓橋始祖陳壽顯赫一些,他是紹興五年(1135)進士,後入職朝廷,因主戰觸怒秦檜,便辭官定居於楓橋,此後在楓橋興教育、辦學堂,培養了諸暨縣內外大批人才,如王厚之等名家就是他培育的。
陳壽曾有《宅步家居感懷詩》三首,其中之一為:“家世南遷自汴京,飄然浪跡寄杭城。卜居宅旁梯山穩,辭身離翰苑輕。驅虜每詢邊將捷,思歸頻夢故鄉情。幾回翹首登樓望,飄渺層雲護禁陵。”關心國事、思念故鄉,無奈寄居異鄉之情在詩中濃濃透出。
經過多年的孕育,元末明初王冕、楊維楨、楊維翰橫空出世;陳氏一族代代有聞人,如陳性學、陳洪綬、陳字、陳遹聲、陳季侃、陳時驥、陳欽,還有現代作家陳海飛等;駱氏一門也不遑多讓,明代駱問禮及近現代駱清華、駱寒超、駱恆光、駱建軍、駱燁等都是楓橋駱氏後人;何氏族人則有何文慶、何蒙孫、何燮侯、何競武、何達人等。
雖然楓橋先前曾是越國都城大部(阜)所在區域,但在歷史記載中卻長時期處於低落或中斷,直至宋朝,楓橋才重新振作。因本文重點在宋朝,對楓橋在其他階段的歷史就不作展開。
建置的設立,人口的聚集,使得經濟和文化得到快速發展,南宋時的楓橋已成為浙東耀目的名鎮大市,“上有楓橋、下有柯橋”就是真實寫照,商業繁榮,教學興起,文化復興,楓橋作為浙江省歷史文化名鎮就這樣層積堆累而成。
二、陸游與東化城寺塔
陸游所居的山陰與楓橋只隔一條古博嶺,陸游多次到楓橋遊玩和旅宿,現在能查到陸游為楓橋寫了三首詩。在介紹陸游三首詩之前,先梳理下楓橋宋代東化城寺塔的由來。

楓橋紫薇山。
楓橋紫薇山上原有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建立的東化城寺,會昌法難被毀,北宋開寶四年(971)復建,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徹底譭棄,不再存在。宋朝堪輿學家認為,這紫薇山雖然秀美,唯其山形像蟄伏在楓溪江畔的一條鯰魚,兩眼突出,覬覦大地,那副闊嘴巴會吞噬生靈,只有在鯰魚背上插上一柄寶劍,才能既利用它的山勢,又鎮住它的邪氣。

宋代東化城寺塔。
古代大多聽信堪輿家的說法。於是北宋元佑七年(1092)在紫薇山上建起了一座玲瓏寶塔,與東化城寺相距不遠,故名東化城寺塔,又因元佑年間所建,又叫元祐塔。塔原高7層,經過風霜雨雪,戰火洗禮,東化城寺塔頑強地生存下來,雖然只存下4層,但塔基和塔身依然還是建造時模樣,塔的磚側有塔型圖案及“壬申元祐七年”的記年銘文,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是浙江省僅剩的6座宋塔之一,1989年為浙江省重點文保單位,2013年列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東化城寺塔是宋代楓橋的史蹟見證,是文化傳承的信仰支柱,是歷史風霜的年輪載體。
東化城寺與東化城寺塔相互映照,儼然是楓橋鎮的一個勝蹟,吳處厚、陸游、朱熹、辛棄疾、呂祖謙、陶望齡、倪元璐、劉宗周、徐渭、陳洪綬等都曾來此遊玩。

陸游(放翁)遺像。
陸游在楓橋寫下三首詩。其中《贈化城寺院僧》是夜宿化城寺所作,詩云:“老宿禪房裡,深居罷送迎。爐紅豆箕火,糝白芋魁羹。粗衲年年補,紗燈夜夜明。門前霜半寸,笑我事晨徵。”
顯然,這是冬季時節所寫。禪院高僧在禪房裡深修,不事送往迎來。房間裡豆箕燃紅爐火,與白晳的芋羹相對應。身著厚厚的百納僧服,秉燭夜讀紗燈下。望外見門前濃霜滿地,老僧微笑送我晨曦遠征。
陸游的《過乾溪橋》詩:“劍外歸來席未溫,南行浩蕩信乾坤。峰迴內史曾遊地,竹暗仙人舊隱村。白髮孤翁鋤麥壟,茜裙雛婦闖籬門。行行莫動鄉關念,身似浮萍豈有根。”
乾溪橋在楓橋鎮東,地控古博嶺,是紹興府與諸暨縣往來主要通道。從詩意不難明白,陸游剛從四川歸來不久,又要奉命南行,雖然留念家鄉親情山水,但還得奔赴供職之地……這詩是陸游路過乾溪橋時所寫。
陸游的《登鵝鼻山至絕頂訪秦刻石》詩:“街頭旋買雙芒屩,作意登山殊不惡……秦皇馬跡散莓苔,如鐫非鐫鑿非鑿。殘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報焚書虐。人民城郭俱已非,煙海浮天獨如昨。”

刻石山(鵝鼻山)新立李斯刻石紀念碑。
鵝鼻山又名會稽刻石山,是諸暨與山陰的界山,一山兩面,屬會稽山脈一座山峰。陸游此詩題目長,引用時省略了。詩意主要描述他攀登鵝鼻山時所聞所見,秦時李斯的刻石字碑“已鐫非鐫”“已鑿非鑿”,面目全非云云。
東化城寺塔與陸游的詩作,是歷史留給楓橋的宋代信物。
三、“三賢”的流風餘韻
“三賢”是宋朝楓橋立鎮以來的文化結晶,其成長活動多在諸暨,身後都長眠他鄉。也許如此,圍繞三人出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謎團,焦點是楊維楨的籍貫眾說紛紜,王冕隱居的九里山到底是哪裡?陳洪綬死後為什麼葬在紹興山陰?對於這些問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發過對應文章,因為這些問題不搞清,將嚴重影響“三賢”研究的深入。

楊維楨畫像。
楊維楨的籍貫,由於《明史》首先搞錯,把其落籍到會稽頭上(籍貫以縣為單元),所以一時竟有山陰人、會稽人、諸暨人、紹興人等,還有兩說並存,語焉不詳等多種說法,且錯還出在《辭源》《中國文學史》《中國人名大辭典》等權威書籍中。為此,我根據原始資料及實跡,對差錯的原因一一理出,寫出考證文章,發表在南京博物院《東南文化》、吉林社科院的《社會科學戰線》上,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成為公認的學術成果。其後,楊維楨的籍貫除了原始文獻只有踵繼原錯以外(如《明史》),其他都得到正本清源,都寫明是諸暨人。

陳侃章《楊維楨籍貫考辨》刊《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第2期。
陳洪綬墓在山陰這個問題不難解決,主要是其祖上墳地在山陰。所以陳洪綬葬在那裡也順理成章。
相對說來,王冕隱居九里山要複雜一些,因為歷史上對王冕歸隱分別有諸暨九里山、會稽九里山、山陰九里山、餘姚九里山、江蘇銅山縣九里山等多種說法。為此我根據原始資料,比對各說,考鏡源流,參閱王冕《竹齋集》,走訪實地,寫成《王冕隱居在哪裡》一文,發表在頗具人文聲望的中國臺灣正中書局《國文天地》1992年總第78期上,逐條排除他說,王冕最終隱居地無疑是諸暨九里山。
二十年以後,南京師範大學程傑教授在《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2年第一期上發表了《王冕隱居紹興城南九里考》文章。我因久離文化行業,對上述情況並不瞭解。後來從事梅花種植的陳樹茂先生告訴我有這麼一篇文章,他認為這個作者太無厘頭了,希望我能撰文澄清。

王冕《九里山中詩》見《竹齋集》書影。
我大感興趣,但看了以後第一感覺:這文恐非署名作者本人所寫。首先題目就主題先行,既已定下王冕是“隱居在紹興城南九里”,還考證什麼啊?其次,整篇文章基本沒有原始資料,對諸暨、紹興歷史地名很不熟悉,只用詩詞作信馬由韁的解釋,左手倒右手的互搏。其三,作者分不清“九里”與“九里山”的區別,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紹興會稽縣沒有“九里山”只有“九里”,而只有諸暨才有“九里山”和“九里村”,王冕隱居的是“九里山”而不是“九里”,僅憑這一點,這所謂的考證文章就不成立。

王冕隱居諸暨九里山之白雲庵。
於是,我迅速撰成辯駁文章,投寄相關刊物,但該刊以“不發起爭論”為由予以婉拒。在寫本篇文章時,我上網偶然看到署名弘蟲的作者,對程傑教授的文章作了全面駁斥,寫得有根有據。我們當然相信程教授有其專長一面,但僅就此文而論,或是疏於深入,或是發揮不佳。
毫無疑問,王冕、楊維楨、陳洪綬是宋代以來彪炳史冊的人物,守護、弘揚、傳播好“三賢精神”不僅僅是諸暨的責任。
楓橋“宋韻”浩浩蕩蕩,時代文化有序流淌,諸暨楓橋以堅實的步伐邁向廣闊的未來。
本文為錢江晚報原創作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複製、摘編、改寫及進行網路傳播等一切作品版權使用行為,否則本報將循司法途徑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