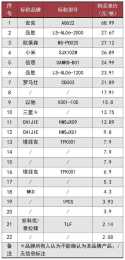當一部電影的導演在接受採訪時說拍天意時,我們不用猜度電影講什麼,而應探尋電影怎麼講。作為元電影的《吉祥如意》,是一部關於電影內容本身的電影,分為兩個部分——《吉祥》講述姥姥死後,一家人如何安置患病三舅的問題;《如意》則展示前一部分的拍攝過程。在虛擬與現實的疊印中,二者互相解釋又互為反諷,在觀眾深情地沉浸於導演建構的想象性秩序時,又不期然地打破第四堵牆,給觀眾以自反性的思考。正如魯迅在《墓碣文》中說:“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導演拍攝元電影的種種敘事策略便是一次次的“抉心”之舉,審判自己的同時也在拷問觀眾:當親情缺失已久,我們是否還知道它原本的味道?
互文:虛實構築的意義之網
《吉祥》中只出現了一位職業演員,即劉陸飾演的王慶麗。作為推動情節、主導敘事的主要人物,劉陸在《如意》中並不瞭解王慶麗的真實心境,因為王慶麗在經歷上保持沉默,從而導致了劉陸飾演的“王慶麗”在“真實”上的失語以及將演員的職業素養和社會的傳統道德融入“王慶麗”這一空洞能指的行為。《如意》中呈現真實的王慶麗對待王吉祥的贍養問題以及家人由此引發的劍拔弩張局面是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而《吉祥》中最富有張力的敘事段落年夜飯,“王慶麗”開始是以演員的身份進入角色,隨著家庭積怨的層層剝開,矛盾最終爆發。本該是團圓和氣的年夜飯,因為“王慶麗”父親的原因而吵得不可開交,演員身份不足以終止這場真實的吵架,所以充滿道德正義感的社會角色試圖進入,併成為傳統孝道價值觀所認同的王慶麗,用下跪磕頭的方式澆滅了這團熊熊烈火。

當然,在《如意》中導演透過與王慶麗本人的交流解釋了造成她與父親疏遠的緣由,並以人物訪談的形式對王家兄弟姊妹進行訪談,揭示促使家族走向分崩離析的錯綜複雜的原因,拓寬了敘事層面,加深了人物深層次的挖掘,進一步與《吉祥》形成互文關係,二者互為因果,在一場葬禮和一桌年夜飯中記錄了親情的零落與悲哀。
凝視:認同引導的分裂之果
《吉祥》以王慶麗的視點轉移來推動敘事,使觀眾在觀影過程中將自身融入故事,忘記了自己是誰,將自己誤認為電影中的角色。此時,銀幕的作用相當於鏡子,在觀影中,觀眾往往將自己投射到角色上,把她看作理想的化身。觀眾對王慶麗處於家庭矛盾中心的處境表示理解與認同,因為現代人何嘗又不是像塊三明治一樣,夾在上一代和下一代的責任與義務、矛盾與苦難、幸福與崩潰的裂隙中危險地遊走。但究其本質,這是“虛幻的像”,而並非觀眾本身,觀眾對王慶麗抱持的是一種“想象性認同”。
隨之而來的《如意》便無情地戳破了這一幻像。它暴露了《吉祥》背後的影像機制,把《吉祥》的幕後拍攝過程直接呈現在後一部分的《如意》中。對於觀眾而言,《吉祥》建構的想象性秩序徹底崩塌,它所努力形成的一個自洽的意義系統淆亂。致使觀眾認為滿足自己在漆黑影院中肆意勃發的窺視欲是虛假的,而對於導演的電影結構設計產生思考。

凝視的主體不僅有想象性認同也有象徵性認同。拉康說:“象徵性認同根本上是對他者的認同,是在他者的位置對自我的觀看,所謂的自我理想不過是主體以他者的目光看自己時得以凝定的形象。”由於《如意》中清晰地呈現導演對《吉祥》的拍攝過程,導致觀眾意識到象徵秩序的存在,又使王慶麗成為象徵界的主體。觀眾發覺這是和自己一樣生活在現實中的真實人物,電影也不是夢工廠。演員劉陸之所以能成為“王慶麗”是她在象徵界替代了王慶麗本人的位置,因而獲得了他者目光的指認,扮演著自己在象徵秩序中被安排的角色。
從想象界到象徵界,觀眾彷彿坐過山車一般,品嚐了理想灰霾下的現實苦果。
自反:理想催生的親情之橋
當影片的某些敘事段落需要轉場時黑場,當導演問及從商業片轉型到文藝片的問題時沉默,當王慶麗被演員劉陸問為什麼十年不回家時無言。這些沒有言語的畫面,其實也是一種言說,缺席是另一形式的在場,此時無聲勝有聲地將普適化的親情問題拋給觀眾:影片中人物的失語,難道現實中我們沒有嗎?——老人的贍養、家庭的利益糾紛等等,我們不希望自己的家庭如影片中的人物,為利益而不顧骨肉親情;不希望老人去世,兄弟姊妹便樹倒猢猻散。一次觀影就像為觀眾敲響警鐘,以否定的形式建立了自己家庭的理想。
同樣,《如意》對《吉祥》部分故事世界的解構,建構起更深層次的話語表達。《如意》中導演談及創作初衷是拍攝姥姥如何過春節以及家庭的溫馨和樂美滿,但計劃趕不上變化,天意使然,姥姥去世,拍攝的內容變成家庭倫理的悲劇和世事無常、人生無奈的慨嘆,這是自反性指涉。《吉祥如意》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元電影,便是因為它經由自反性指涉這一橋樑,引導觀眾的思索抵達橋對岸的人性之真、親情之美以及人類生活生存的本然狀態。

我們看到《吉祥》在《如意》的框架內浮現出真實的殘忍、荒誕的反諷——飾演的王慶麗反而比王慶麗本人更具有人情味兒、更具備女兒對患病父親應有的態度和感情;本該一團和氣,其樂融融的年夜飯卻變成矛盾爆發、親情消散、使氣鬥狠的修羅場;家人的來齊團聚不是因為姥姥的去世,而是導演需要拍攝關於本家的影片;當全家福拍完後,王慶麗照舊回到城市,王吉祥則帶著氈帽在大雪紛飛中落寞地踽踽獨行。
但我們要知道真實的殘忍背後是理智化的情感與形式化的生活,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博弈權衡的結果。影片的敘述會更好地讓現代人去理解所謂的殘忍,去體會即便如此,依然有勇氣和擔當面對未來的生活。影片看起來好像不那麼“吉祥如意”,但“吉祥如意”的缺席,恰恰召喚著觀眾對“吉祥”的祝願,對“如意”的祈禱,希求在溫情的綠洲裡沐浴良善的光輝,抵禦人性荒原的侵襲,呼喚現代人缺失的親情迴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