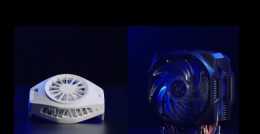摘要:漢文帝霸陵有別於西漢諸陵的一個重要文獻記載,不僅是其選址於白鹿原上,而且還“因山為陵,不封不樹”。對於這一文獻記載的理解,時人的初心與記敘和後世的流傳與解釋漸行漸遠,最終導致產生文帝霸陵本為“崖墓說”的推測。江村大墓的考古發現,初步揭示了漢文帝霸陵的真實情形,但同時也提出一系列新的問題:究意是歷史文獻記載有誤?還是後人的理解出現誤讀?霸陵葬製出現的原因為何?對於後世又有何影響?本文結合文獻和考古兩方面的材料,擬對這些問題進行新的闡述。
關鍵詞:西漢陵墓;帝陵制度;漢代考古;薄葬習俗;江村大墓
一、漢文帝霸陵的文獻傳承
與考古調查
西漢立國達215年,共有十一座帝陵。其中九座位於渭河北岸的咸陽原上,另有兩座位於今西安的東、南郊,一座是文帝霸陵,一座是宣帝杜陵。迄今為止,對於咸陽原上九座西漢帝陵的考古調查所取得的主要成績之一,在於澄清了諸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順序,對於自北宋宋敏求《長安志》到南北朝時期佚名《三輔黃圖》、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清初畢沅《關中勝蹟圖志》等文獻記載的誤定、誤釋進行了修正。在確定九陵的方位、排列順序之外,也基本上廓清了陵墓封土結構、陵園垣體與門闕、陪葬墓、從葬坑等考古遺存的情況[1]。
但是,關於漢文帝霸陵的相關情況,直到1984年,黃展嶽先生還只做了這樣的描述:
“霸陵‘依山為陵’尚未勘察。陵南薄太后墓、竇皇后墓尚存。1966年曾對竇後墓進行勘察,併發掘從葬坑四十七個。”[2]正是因為文獻上有霸陵“依山為陵”這一記載,加上歷來的考古調查和研究都未能發現地面上的封土,所以霸陵可能為“崖墓說”便因之而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可舉徐蘋芳先生所述:
霸陵“因山為藏”的形式,從外觀上看是“因其山,不起墳”;西安東郊鳳凰咀的高崖,即是霸陵之所在。從墓室的結構上來說,應當是一種崖墓。西漢時這種“因山為藏”的崖墓,如山東曲阜發現的西漢魯王墓、河北滿城發現的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皆屬此類。霸陵即是崖墓,估計應與上述兩墓的形制大體相似。[3]
隨後,黃展嶽先生也持相同觀點,認為西漢諸陵內部的構造因未發掘尚不清楚,但從已經發掘的西漢諸侯王墓的情況來看,“這種築有高大墳丘的帝陵,應類似北京大葆臺燕王墓、長沙鹹家湖長沙王墓,作豎穴土坑,多層棺槨,棺槨外設黃腸題湊及若干外藏槨室的形式。霸陵依山為陵,應類似河南永城梁王墓、河北滿城中山王墓和江蘇徐州楚王墓的形式,在山腹內鑿出甬道、墓室、迴廊,設定多側室、多耳室”[4],也將霸陵歸入到“崖墓”這一型別。
按照這個推測,在長期以來考古調查當中,對於灞河西側“鳳凰咀”所在的高崖進行過多次考古鑽探,但迄今為止卻尚未發現任何建築墓葬的遺蹟。那麼,有關漢文帝霸陵的文獻記載究竟給後人提供了什麼線索?這些線索是否為“崖墓說”找到了足夠的證據呢?我們有必要對相關的文獻記載再作一次梳理。
關於霸陵的營建,文獻史料首見於漢代司馬遷《史記·孝文字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5]其後,東漢人班固所撰《漢書·文帝紀》記載與《史記·孝文字紀》所記完全相同:“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6]與之同時代的《漢書·楚元王傳》記載:“孝文寐焉,遂薄葬,不起山墳”[7]。《後漢書·王符傳》載:“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8]。
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文帝霸陵的文獻記載仍不時見諸文字。如佚名《三輔黃圖·陵墓》記載:“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就其水名,因以為陵號”[9]。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渭水》條下載:“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10]其後,在一些史料中也透露出關於漢文帝霸陵的記載。如宋人王茂撰《野客叢書》記載:“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11]另如《雍錄》記載:“文帝嘗欲馳車下霸西峻坂,因袁盎諫而止,即白鹿原之西坡也。帝樂其地遂即霸上立陵,以為霸陵。陵後又置縣,是為霸陵縣也。”[12]
從以上所列文獻,可以歸納出所記文帝霸陵的主要建造特點:其一,是“不起墳”或“不起山陵”,即在地面上沒有墳丘,這和西漢其他諸帝陵均在地面築砌有高大的覆鬥型封土明顯不同。其二是“因其山”,或與上文相連理解為“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其三,是實行“薄葬”,具體而言即隨葬品儉約,不用金銀銅錫類器物隨葬。其四,與陵墓共存的,還設有為其服務的陵縣之屬。
這四個特點當中,第一、第二個特點和以往的西漢諸陵相比較最顯差異,後世通常是將兩者合二為一,總體理解為“因山為藏,不復起墳”,除了地面不建墳丘之外,還將山崖作為藏身之所,將墓葬深藏於山崖之中。正是基於這一理解和認識,也成為考古學界多年來推測漢文帝霸陵可能為一座“崖墓式”的帝陵重要的文獻依據。
二、江村大墓的考古發現
及其啟示
繼1966年以來在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白鹿原上發現西漢竇皇后陵園及其從葬坑之後,2001年,在竇皇后墓西側又發現了一座已經多次被盜過的大墓(簡稱“江村大墓”)[13]。據報導“這座大墓墓室長寬各約40米,深約30米,有三道迴廊,緊貼墓壙砌有一週磚牆,牆內為枋木壘築的外槨,外槨與第二週枋木牆之間為寬、高各約2米的外迴廊,廊內堆積有大量的木炭,第二週枋木牆一端設門,內為第二道、第三道迴廊。盜墓者共盜出近300件文物,其中有6件著衣式黑色陶俑”。正是這座江村大墓的發現,使得人們重新討論漢文帝霸陵的陵位所在。近年來陝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據江村大墓的有關情況,得出“此墓位置顯赫,規模大,外藏坑數量多,遠遠超過了諸侯王墓的等級,墓主可能就是漢文帝”的推測,並認為霸陵的墓葬形制可能為一座帶有四條墓道的“亞”字形豎穴土坑墓,與其他西漢帝陵並無兩樣,只是未建封土而已[14]。具體而言,研究者提出了五點論據。
其一,從地貌上看,江村大墓所在的白鹿原東北部雖然沒有西漢其他諸陵所在的咸陽原那麼開闊,但地勢高亢,臺地較為平整,完全能夠滿足建陵的需要。
其二,按照西漢帝陵傳統與制度,帝、後實行“同塋異穴”合葬制度,即帝、後陵均應位於同一陵園內。換言之,文帝霸陵應與竇皇后陵相距不遠,而江村大墓正好符合這一規制。如果將過去選定的鳳凰嘴山崖作為霸陵所在地的話,則與竇太后陵之間兩者相距達2100米,顯然不符合西漢帝陵制度。
其三,西漢帝、後陵一般東西排列,“帝東後西”制是西漢帝陵的主要模式,而“帝西后東”制是次要模式。江村大墓的位置位於竇皇后的西南側,也大體符合這一規制。
其四,西漢帝陵制度中除部分後陵為“甲”字形、“中”字形之外,更多的帝、後陵是帶有四條墓道的“亞”字形豎穴土壙墓,竇皇后陵有高大的覆鬥形封土,與其他後陵沒有差別,故推測霸陵也為一座帶有四條墓道的“亞”字形豎穴土壙墓有所依據。
其五,《水經注》記載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應是陵園內的排水設施,西漢帝陵中在漢景帝陽陵、漢武帝茂陵中都曾發現過相同的遺蹟,但在後陵陵園中尚未發現排水設施,這一點或可成為界定帝、後陵園的依據之一。
這一新的觀點很快引起學術界的關注。雖然江村大墓尚未經過正式的考古試掘,但根據其周圍發現的大量外藏坑、與竇太后又同處一個陵園之內、自身的規模十分宏大等這些要素加以綜合考慮,江村大墓就是漢文帝霸陵的這種可能性陡然上升。這個時候,我們再來重新審視文獻記載所提供的線索,也會得到一些新的啟示。
漢代的文獻記載中,都提到漢文帝霸陵“不治墳” “不起山墳” “不起山陵”這一點,即強調了霸陵在地表不起高大的封土(即山墳、山陵)這個特點,這和江村大墓的情況大體上是一致的,目前在江村大墓墓上尚未發現明顯的封土遺蹟。所以,文獻記載和考古蹟象兩者之間是基本吻合的。但是,文獻中也沒有提供任何霸陵採用了“崖墓”之制的線索,反倒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史記》《漢書》中都特別強調了漢文帝臨終前的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所謂“因其故,毋有所改”,應當理解為他不希望看到霸陵的山川景象因為治墳營陵的舉動而有所改動和破壞。再進一步,在《史記》和《漢書》當中,也找不到司馬遷、班固本人用過“因山為藏” “因山為陵”等字句的跡象——這原本是後世推測漢文帝陵墓採取了“崖墓”埋藏方式最為重要的文獻依據,現在看來就需要再加辯識了。
《史記》裴駰《集解》和《漢書》顏師古注均引用了東漢學者應劭對漢文帝遺詔中“霸陵山川因其故”這一句的解釋:“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15]可見文獻中最早出現漢文帝霸陵“因山為藏”的表述,始於東漢末年的應劭。
如果僅僅只看“因山為藏”一句,在此至少可以作兩解:一是依託山脈、緊靠山脈作陵;二是以山為陵,建陵其內。如取前者之意,則只是說霸陵的選址依山靠水,並且不再另起墳壠;如取後者之意,則可理解為霸陵建陵于山體之內,以山為陵而不起墳丘,後來推測霸陵為“崖墓”者,應當是從後者之意來加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聯絡到應劭註釋下文中還有“山下川流不遏絕也”一句來看,正是因為漢文帝霸陵的營建工程沒有大量的動土而導致自然景觀的巨大改變,才會產生這個結果。換言之,霸陵的營葬只能在既沒有開鑿山崖,也沒有壘砌高大封土的情況下,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山川景象如故,山下川流也不致遏絕的局面,而這個局面,正符合漢文帝臨終遺詔的本意。
所以,回溯文獻,應劭所釋的“因山為藏,不復起墳”一文的原意,應是依託山脈、緊靠山脈建造陵墓,而且不再另起墳丘的意思,與在山體內開鑿墓室並無關係,後人將“因山為藏”理解為營建“崖墓”,看來可能是一個誤讀。
通觀《史記》《漢書》之後的文獻記載,也基本上沿襲了漢代史家的說法,並無新的解釋。只有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渭水》條下記載霸陵“有四出道以瀉水”,有別於其他文獻,這究竟是指霸陵陵園內有排瀉洪水的設施,還是指霸陵封土之上有四條排水道,目前從考古發現的情況還無法確認,前文已經指出,有的考古學者傾向於認為這可能是指在陵園內設定排水溝一類的設施,可備一說。但無論如何,結合江村大墓的考古發現來看,漢文帝霸陵採用“崖墓”一說的文獻依據是不充分的。至於江村大墓本身是否就是漢文帝的霸陵?這還需要考古發掘之後才有可能最後確認,考古學者推測霸陵很可能是西漢帝陵中一座沒有構築地面大型覆鬥形封土、只是在地下采用了四出墓道的“亞”字形大墓這種新的認識,和傳世文獻記載之間並無矛盾,從理論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三、漢文帝霸陵營葬觀念
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如果上述考古發現和文獻史料之間的關係可互為印證,說明漢文帝霸陵並非為一座崖墓,而只是一座不起封土的地下大墓,那麼接下來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漢文帝為何要一改西漢帝陵以覆鬥型封土作為帝陵標識的作法,而採用“因山為藏,不復起墳”這樣一種新的規制呢?究其原因,我認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加以考慮。
第一,是漢文帝對前人“厚葬”風習的反對。這需要聯絡到漢文帝臨終前所表達的願望來綜合考察。《漢書·文帝紀》載:“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臣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鹹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16]這裡,他明確表達了對當下之世“厚葬”風習的反對,也明確表示他將在生後放棄這種厚葬之俗。
戰國秦漢以來,厚葬風習日盛。其中,在地面建立高大的墳丘即為厚葬的標誌之一,又以帝王陵墓為最,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秦始皇陵的營建。秦末漢初天下動盪,有著顯著地面標誌的帝王陵墓遭到大規模盜掘的景象,對於漢文帝而言可謂印象深刻。所以,採取在地面不建墳丘的作法,一方面是最為直觀的對厚葬之俗的捨棄,另一方面從客觀效果上看,也是對死後葬身之所的一種保護方式。《唐會要》記載,當唐太宗貞觀九年因唐高祖駕崩召群臣議定山陵制度時,秘書監虞世南還曾列舉出漢文帝的這段往事來主張推行薄葬:“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帝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夫,以北山之石為槨,用紵 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可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17]。從這條史料可見,漢文帝行薄葬之禮,有其時代背景和更深層面的考慮。
第二,是漢文帝所倡導的“欲為省,毋煩民”的基本國策。《史記·孝文帝本紀》記載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18],《漢書·文帝紀》中班固對此的贊文與《史記》完全相同[19],都提到漢文帝之所以“不治墳”的直接理由之一,就是“欲為省,毋煩民”。
聯絡到漢初“文景之治”的歷史背景來看,《漢書·食貨志》記載漢文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20],班固讚頌他“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締,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21],看來也並非一味諡美之詞。漢文帝霸陵雖然並不像文獻記載的那樣清貧,後世盜墓也從中出土過珍寶之器[22],根據《史記》《漢書》所載,營建霸陵時動員的人力也有“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槨穿復土屬將軍武”等相當規模的陣容[23],但相對秦漢時期的其他帝陵而言,漢文帝霸陵在地面未起高大墳丘,沒有動員更為眾多的民力從事土木工程,從目前的考古遺蹟來看也應是事實。這和漢文帝尚行節檢,無煩民力的治國理念是相互吻合的。
第三,可能與漢代風水術的興起有間接的關係。前舉《史記》《漢書》中還提到一句漢文帝的臨終遺囑,也很值得重視,即“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這句話可以理解為漢文帝希望他所選擇的霸陵作為死後葬地,山川景色一如舊故,不作改動,這當中或許也包含有保持其葬地風水不致破壞流失之意。從時代風尚來看,風水葬地之術在秦漢以來開始興起,凡挖山掘崖之類,按照風水術師的說法,若經營不慎都會洩露風水寶氣,破壞“龍脈”。作為帝王陵寢所在之地,可能在葬地的選址和營建上都更為講究。《水經注·渭水下》記載:“漢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為初陵,以為非吉,於霸曲南亭更營之”[24],便是一個例證。雖然我們目前對於西漢帝陵在選址、營建、築墓等一系列過程當中究竟有多大程度受到漢代地理風水之術的影響,還缺乏更多的線索,但從漢成帝營造延陵來看,應是經過“相地”之類風水擇地之術來預測其吉凶的。以此推之,漢文帝霸陵的建陵過程中受到風水思想的影響,不主張大動山川以改其風貌,也當在情理之中。
漢文帝霸陵從目前所獲江村大墓的考古情況來看,可能是一座沒有大型覆鬥形封土、具有“亞”字形四條墓道的大墓,而不是一座開鑿在山崖之內的大型“崖洞墓”已如前述。漢文帝臨終前下詔不取厚葬,所行之葬禮在當時已算是“薄葬”,這種喪葬觀念對後世產生了長久而深遠的影響。漢以後帝陵營葬凡舉薄葬者,多以文帝霸陵作為其楷模。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三國曹氏的喪葬觀念和考古發現的曹操高陵,當中均可窺見漢文帝霸陵營葬觀念的深刻影響。
據《三國志·魏書》記載,曹操生前在營建壽陵時,便詔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25]在他臨終之前,也實行薄葬:“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26]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因高為基,不封不樹”,這實際上就要將陵墓選址建在高亢之地,利用自然的山麓作為墳丘或象徵高大的墳丘,而不另在地面起墳和樹立任何標誌。這與漢文帝霸陵所主張的喪葬觀念是一致的。曹操的這一喪葬觀念,到魏文帝曹丕時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光大。在曹丕臨終之前,更是在其“終制”中留下遺言:
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自古以來,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27]
根據曹丕的這篇臨終遺言,在其死後文獻記載“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28]。在他的遺言中,將漢文帝霸陵和西漢其他諸陵對舉並列,指出霸陵之所以能夠在漢末的戰亂中得以保全而未遭盜掘之禍,就在於沒有“厚葬封樹”,而其他漢氏諸陵卻未能得以倖免。
近年來,曹操高陵(發現時稱為“西高穴二號墓)的發現為文獻和考古兩方面的對照提供了難得的樣本。曹操高陵位於河南安陽市西北約15公里的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建墓之所地勢高亢,墓上沒有發現封土,墓葬平面呈“甲”字形,為一座多室磚室墓,由墓道、磚砌護牆、墓門、封門牆、甬道、墓室和側室等部分組成。由於墓室多次被盜,當時隨葬器物的真實情況已經不得而知。從殘存的隨葬品來看,仍有金器、銀器、銅器、鐵器、玉器、漆器、陶瓷器和石器等遺物約400多件,其中包括能夠反映墓主人身份的刻銘石牌和具有時代特徵標誌的鐵甲、劍、帳架等物,由此被學術界多數人認定即為曹操高陵[29]。
在曹操高陵發現之後,2016~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為配合高陵的保護展示工程,又對高陵陵園及建築遺蹟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結果表明,高陵陵園為內垣牆外壕溝結構,M2即曹操墓為陵園的中心,神道位於陵園東部,寬約5米,南北兩側均有柱礎標記,現存東西長約33米。神道北部、南部有對稱的建築遺蹟,陵園南部也有功能不同的建築遺蹟發現,從陵園內發掘出土有筒瓦、板瓦等建築遺物,瓦當上裝飾的蘑菇狀雲紋與洛陽白草坡東漢帝陵陵園遺址出土瓦當紋飾相似,可確認其年代為東漢中晚期[30]。
將曹操高陵和現在“疑似”的江村大墓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兩者有若干相似之處:其一,兩者最大的共同特點,就是“不封不樹”,即在墓上不建高大的墳丘;其二,都將陵墓選址在高亢之地,借山勢而顯其尊貴,利用自然環境而不另作改造;其三,兩者都建有陵園。江村大墓位於陵園內竇皇后墓西側,曹操高陵的陵園與洛陽東漢帝陵陵園相比明顯較小,顯然不是按照帝陵規制營建,但地位也較特殊,位於陵園中心位置;其四,雖然文獻明文記載漢文帝和曹操都下詔行薄葬,但從漢文帝霸陵在晉代被盜掘的情況以及在曹操墓內仍有作為隨葬品的金銀銅鐵器物發現來看,表明既使是所謂的推行“薄葬”,主要還不是體現在隨葬器物的多寡或品級高低上。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初步的結論:漢魏時期由漢文帝首倡的帝陵“薄葬”之禮,最為重要的標誌就是“因山為藏,不復起墳”。也就是說,不在地面上遺留下來秦漢帝陵最具威儀、等級和皇權象徵意義的高大墳丘——即文獻記載的所謂“山陵”。但在地下墓室的營建、隨葬品的多寡與種類方面,既使有所限制,也並非文獻記載的那樣嚴格。
對於“因山為陵”這句話的理解,也需要結合考古遺存加以重新認識,過去認為這意味著是漢文帝霸陵是將墓室開鑿于山體之內,以山體為藏身(屍)之所,從而進一步推測其可能暗示著這類帝陵為大型“崖洞墓”的看法,也應隨之加以必要的修正。
不過,如同河北滿城漢墓那樣真正開鑿在山體之內的崖墓在漢代的大量出現,也是一個值得深入加以探究的問題,它的源頭就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並非源於漢文帝霸陵的可能性隨著江村大墓的發現而增大。當然,漢文帝霸陵就是江村大墓的推測,也還有待於江村大墓最終的考古發掘結果才能揭曉。如果筆者上述的觀點可以成立,那麼,對於漢代崖墓起源的真正原因及其源流演變的過程,還需要結合漢代墓葬制度和喪葬禮俗的發展變化,以及地域文化、甚至外來文化影響等多方面的因素重新加以探討,才會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作者:霍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另此處省略註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1年第6期)
責編:段姝杉
稽核:方 勤
陳麗新
——版權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