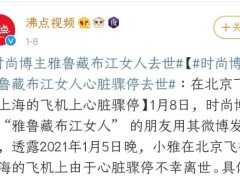近年來的韓國電影總是給人驚喜。前兩年,李滄東的《燃燒》雖無緣最後的大獎,但卻以3。8分的高分打破多年的戛納評分記錄,熱度極高;而今年奉俊昊則以《寄生蟲》一舉拿下金棕櫚大獎,打破韓國電影多年來在此項大獎上零的紀錄,並且更是在此後的世界多個電影節上橫掃各項大獎。
韓國電影自其第二次振興浪潮以來,其對現實問題大膽暴露的現實主義風格一直影響至今,《熔爐》《素媛》《7號房的禮物》等一系列影片讓電影真正成為“能改變國家”的藝術。這部《寄生蟲》更是以一個戲劇化程度極高的故事撕開社會和諧的假面,用一個韓國故事,直指當下世界多國普遍存在的階級差距、貧富分化等問題。這一次,它不只是想改變一個國家,其所關心的是整個人類社會。

《寄生蟲》採用三一律的形式,整個故事的時間地點高度集中,矛盾衝突緊張激烈。導演以利落的敘事風格講述了一起發生在一所高階住宅內的隨機殺人事件。男主角基宇在朋友的引薦下進入富家樸社長家成為英文家教,然後在一系列計劃下,基宇一家四口隱瞞關係分別進入社長家任職。前幫傭雯光失業後在社長全家外出的晚上返回,揭開丈夫住在地下室的秘密,偷聽的基宇三人不慎摔下臺階,基宇一家的秘密也被撞破,由此展開了矛盾衝突。

誰在寄生?
電影名為“寄生蟲”,這個名詞在片中具有豐富的指涉意義。毫無疑問地,每個觀眾都能看出基宇雯光等人是社長家的寄生蟲,即窮人依靠富人的需求才能維持自身的存在,窮人寄生於富人。導演奉俊昊在一次採訪中說,其實社長一家也要依靠雯光這樣的傭人們才能正常的生活,他們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寄生蟲。片中坐在車裡的社長對司機說,家裡沒有了幫傭,要不了幾天就會變成垃圾場,因為太太什麼也不會做。由此,富人依靠窮人維持正常生活而成為“寄生蟲”也不難理解。畢竟,馬克思曾經說過,社會性是人的根本屬性,沒有人能完全獨立地活著。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寄生蟲”。但這兩層意義上的寄生,至少是當事人有自知的;更為可悲的是那些潛藏的、不自知的寄生。就在社長說完“她什麼也不會做”後,司機問他,“儘管如此,您也依舊愛您的太太,不是嗎?”一聲的虛假做作的笑後,社長說了一句“我當然愛她”。多麼可笑。他愛她什麼呢?她不過只是一個既可以擺在家裡又可以帶到人前的花瓶,她對他唯一的價值就是順從和麵子。
她看似是住在高級別墅裡的富太太,但實際上只不過是寄生於一個並不真心愛她的富有男人,靠著順從過活的金絲雀。這樣的她,和家裡的三隻整天只對著社長搖頭擺尾的狗,有什麼區別呢?而她對這一切並不知情,並且顯然,還充滿天真的滿意。諷刺的是,當我們跳出電影時,我們驚訝地發現現實生活中有多少女人或是男人在費盡心計地想成為她。

馬太效應
有時,寄生是互利互惠的和諧共生;但有時,寄生卻是“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你死我活。放在更大的人類社會層面來說,經濟和社會學家們稱之為“馬太效應”。吳勤世當年因為開古早蛋糕店生意失敗破產無力還債而被逼躲進地下室,基宇一家也是在小生意失敗後陷入生活的困境。而當他們在為了寄生於社長家的機會而爭得頭破血流時,卻沒看到導致他們走到如此地步的真正原因。
正是因為像樸社長所在的這樣的IT及各類新興企業的強勢發展,整個社會的經濟格局發生快速變化,那些無法及時適應的個體,由於利益空間被迅速擠壓,於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敗的命運。在此過程之中,社會財富更多向資本聚集,貧弱的個體想要重新發展變得更加困難,貧富差距由此不斷加大。但這些是身處底層的基澤和吳勤世們所無法知曉的,當馬太效應顯現時,他們只能為了更卑微的寄生機會而拼命爭奪。一個好的社會,壞人也再無心作惡;而反之,好人也不得不觸發人性中惡的開關。而如果說,吳勤世和雯光想留在社長家只是為活命和守護夫妻親情,這樣的願望尚且是人的生存本能的話,那麼已經進入社長家幫工後,基宇一家的願望則就該說是悲劇。

轉運石
魯迅說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對經歷過失敗的人來說,東山再起的希望就是最有價值的。生意失敗、家境陷入困境的基於一家在進入社長一家工作後,他們並不滿足於此。他們想要的,或許更多。酒桌前,基宇表示想要和多慧交往並娶她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贊同和更大的期許:他們想要和社長一家成為朋友,成為親家。他們,想成為上層人。作為觀眾,在螢幕前看著這一幕會不由得在心裡暗自嘲諷他們的痴心妄想。可是,螢幕內的他們彼時彼刻卻是那般天真的相信其實現的可能。
不管是基宇的富家同學送給他的山水盆景石頭/迷信、還是他和爸爸說“我一定會考上這所大學”的堅定想法/升學、以及基澤和忠淑所期待的和富人建立真正的朋友和婚姻關係/社會關係攀附,這些其實代表了基澤一家這樣的底層人所認為的社會階級流動的途徑,更確切來說,是底層人的階級上升通道。但這部電影真正殘酷的地方就是接下來的場景:躺在沙發上的社長因為聞到了藏在桌下的基澤身上的味道,而由此和妻子談論起他的“越界”。
幾句話聽下來,基澤此前所有的“痴心妄想”都被打碎。因為他清楚地意識到了在上層富人的世界裡,人與人之間是有鮮明界限的,那些搭地鐵的下層人,更不必說窮人,是永遠無法真正和富人成為朋友的。他們不希望更不允許窮人下層人去“越界”,那些所謂的上升通道原來是那樣虛幻和脆弱不堪。人性在那一刻是如此的真實和赤裸。

當基澤躺在避災的體育館裡時,他對基宇說,“人不該有計劃,如果一開始就沒有計劃的話,那就發生什麼都無所謂了。”這裡的計劃,其實就是希望。認清曾經滿心寄託的上升通道的現實不可能性讓基澤徹底絕望。
兩組對比鏡頭,即吳勤世和雯光在地下室的掙扎與基澤父女三人在逐漸被淹沒的家中搶救,以及準備開派對的夫人打扮採購過程的從容和被邀請的基澤一家的慌亂窘迫,更是鮮明地揭示出不同階級之間鴻溝的難以逾越。相比貧富和階級的巨大差距,階級固化是更大的悲劇。因為它讓既得利益者活在能一直維持現狀的美夢裡,讓那些普通的底層人徹底失去人生所有的希望。正因為失去了希望,所以在當社長不顧垂危的基婷而冷漠地索要鑰匙,又因為聞到了吳勤世身上同樣的味道,捏著鼻子去撿鑰匙的時候,基澤才會毫無情緒又可以說是近乎本能地向他紮下了那一刀。然後直接逃進了地下室,那個真正屬於他的棲身之所;他也最終實現了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窮人。
這正如電影《燃燒》的最後,在認清了生活現實的令人絕望和失去了自己喜歡的女孩子後,李鍾秀選擇殺死本。這種極端選擇不是因為基澤和鍾秀這樣的人本身有多壞,而是因為在被僵死現實逼到無路可走時,這是他們剩下的唯一本能。只有在死亡面前,不同階級間的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

影片最後,基宇寫給爸爸的信中說他要賺很多錢買下那棟房子,到那一天,爸爸就可以從地下室走出來了。兒子是曾經還懷有希望的父親,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在更大機率上,窮其一生,他可能也買不下那套房子。而爸爸,也永遠不會再走出地下室,不只是因為他不能,更是因為他不再想。雪崩來臨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但我們更希望的是,在悲劇無法挽回的那一天真正來臨之前,能有更多的人覺醒,來實現對整個社會現實的改變,讓爸爸能在有生之年的某一天,真正地走出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