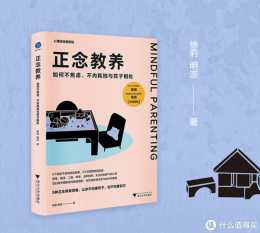十年前,我談歷史文化名城,在通用的“經營”與“打造”之外,添上了“養育”一詞:“人需要養育,城也需要養育——包括體貼、呵護與扶持。這是人文學者與工程師或經濟學家不一樣的地方。在我看來,城市不僅是外在於人的建築群,而且是人及其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今天把話題倒過來,城市需要養育,人才也同樣——或者說更加——需要養育。待人如此,待己也不例外。這裡說的不僅是治學方法,更包括人生境界。唐人韓愈《答李翊書》中的名句,除了“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以及“惟陳言之務去”,還有對於“仁義之人”的期待:“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所謂“養其根”,讓我想到的是孔子的“遊於藝”。朱熹《四書集註》稱:“遊者,玩物適情之謂。”也就是說,優遊其中,涵泳性情,如同魚兒在水中自由自在,其樂無窮。學無止境,一味強調苦讀不行,必須自得其樂,方能持之以恆。

視覺中國供圖
這裡的“遊”,除了“求學”與“修心”,某種程度上還包括“養生”。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寫過一組“學術隨感錄”,其中有一則《不靠拼命靠長命》,講的是王季思和夏承燾的故事,自我調侃中,不無理趣與深意。當初的解釋是:“學術研究不比文學創作,不能僅憑靈感與才氣,還需要大量的經驗和知識積累。有二三十歲的大詩人、大畫家,卻極少有二三十歲的大學者。越是研究古老學科,成名就越晚——單是把前人留下的遺產清點一遍,就必須花去多年工夫。因此,‘多快好省’這口號,在學術界是頗為忌諱的。”
人受基因以及諸多內外條件的限制,不是你想長壽就能長壽的。我只是提醒,學問中人,須珍惜自己的身體,不主張一錘子買賣。“風物長宜放眼量”,那是一種難得的境界,值得追摹。我在研究學術史中注意到四位史學大家陳垣、呂思勉、錢穆、饒宗頤,呂思勉比較遺憾,只活了74歲,可也過了“人生七十古來稀”;其他三位,陳垣91歲,錢穆95歲,最長壽的饒宗頤超過一世紀,實歲101,按他自己的計算,應該是“積閏享壽104歲”。是否長壽,基因無法掌控,經驗也不太可靠,但教訓卻是實實在在的。饒宗頤稱“我對自己的身體很珍重,很珍重”,具體表現是:“我自十四歲起,學習因是子靜坐法。早上沐浴、靜坐,然後散步;晚上九時,必寬衣就寢。”如此按時起居、動靜相宜的生活節奏,保證其有很好的體力與精神,長期全身心地投入學術研究。在接受學者施議對採訪時,饒宗頤談及自己如何在強烈求知慾的驅使下,學會一種又一種文字,研究一個又一個問題。這一過程,要很有耐心,有些問題,慢慢研究,竟花費了十幾年。
對於人文學者來說,即便天賦很好,也很努力,學問同樣需要慢慢滋養,因而治學時間長短很關鍵。年歲太大,精力不濟,學問做不動,那是常態,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是也。對於具體學者來說,儘可能保持好的身體與心態,以便延長學術生命,也算是“責無旁貸”。
為什麼說學問是“養”出來的,各人理解不同,有人注重方法,有人強調目標;還有人突出家境及文化氛圍,比如呂思勉和錢穆原為小學教師,足見東南人才之盛;陳垣和饒宗頤出身商人家庭,尤顯近代廣東風氣變化。
比起“養”更難說清楚、也更值得引申發揮的是“活”。所謂“活”出來的精神,除了人要長壽,還得有精氣神。蘇東坡詩云:“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一般來說,演員年輕漂亮,學者則老來好看,那是因為書讀多了,變化氣質,在相貌上也都能呈現出來。排除不可抗拒的疾病侵襲,學問確實能養人,起碼顯得不俗,神清氣爽,從容舒展。在這個意義上,學問不僅體現在著作中,也寫在臉上。這是我對很多老輩學者的直觀感覺,不見得每個人都讚許,但相信很多人會有同感。
陳垣、呂思勉、錢穆、饒宗頤這四位學問大家,主要從事史學研究;而我出身中文系,“談文”遠比“論史”得心應手。同樣辨析師長輩的學術貢獻,談吳組緗、林庚、季鎮淮、王瑤的治學路徑及其得失,我比較有把握。至於陳垣等先生的史學著作,我只是一般性地閱讀,無力深入其學問堂奧。既然如此,為何還要趕鴨子上架呢?那是因為,我關心的主要不是他們的具體學問,而是他們做學問的姿態及趣味,以及背後蘊含著的教育史及學術史的大問題。(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原標題:“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學問為何需要“養”)
流程編輯:u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