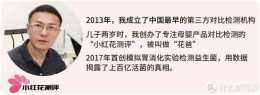如果僅看艾基的簡介,一個生活在二十世紀的楚瓦什語-俄語詩人,一直受到主流文學界的排斥,直至他的晚年即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才被廣泛接受,那一定是東歐米沃什或扎加耶夫斯基那樣的詩人,即具有“批評的激情”,或者說,寫著一種具有社會-歷史批評意義的詩。但讀到艾基詩歌的時候,他完全是另一種風格。如果說二十世紀以來的詩歌主流是批判的或懷疑論的,從艾略特、奧登開始到米沃什,那麼,現代詩還有一個微弱一些的傳統就是讚美的。用批判與讚美(甚至也可以換成理智的與迷醉的)這樣一對概念,只是為著尋找一個參照框架來談論艾基獨特的寫作。畢竟,批判的詩歌也會像扎加耶夫斯基那樣,“試著讚美這個遭損毀的世界”。

根納季·艾基(1934—2006),俄羅斯詩人、翻譯家,1934年生於蘇聯楚瓦什自治共和國沙伊穆爾金諾,1991年出版首部俄語詩集《在這裡》。曾榮獲法蘭西科學院獎、安德烈·別雷詩歌獎、帕斯捷爾納克詩歌獎等。
不過可以簡括地說,批判的詩通常都涉及社會-歷史範疇,富有一種歷史洞見,而讚美的詩一般而言,都與物性-自然密切相關,表現出對元素式自然的深沉迷醉。後者決非一般所說的鄉土詩歌或過期的田園詩,而是具有宇宙論色彩的自然之歌、前蘇格拉底哲學式的元素之歌。這樣的讚美詩意味著一種具有思想史意義的“物性論”。如果說有些讚美的詩——如聶魯達的《馬楚比楚高峰》或帕斯的《太陽石》——也涉及歷史,那麼它的歷史意識可能是長時段的“人類歷史”,而非指向當下的社會-歷史狀況,不是切身的社會體驗,否則,批評的激情就會是它的基調。

《曠野—孿生子:艾基詩集》,[俄]根納季·艾基,駱家譯,雅眾文化|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2年8月。
曠野與神殿的視同隱喻
就個人生活而言,迷醉於元素式的大自然遠比清醒的歷史心智更接近歡悅式的生存。在一個機械論或電子時代,仍然能夠書寫宇宙論-自然的詩人是幸運兒,一般而言,他們都得到了自然額外的恩賜,不只是他們通常生活在社會的邊緣,還應該得到了自然-物性的祝福。我們知道,有頌歌傾向的詩人如埃利蒂斯、聖-瓊·佩斯,他們的少年時代都生活在廣闊的海洋世界,生活在明淨的海島上,有如置身於宇宙的黎明時刻。艾基生活的環境,我們可以從他的詩中看到那所“朝向曠野的房子”,周遭是無邊無際的“曠野”。當然可以補充一些詞或置換一些詞彙,“荒野”,“森林”,“樹”,他的基礎詞彙仍然是那麼少,光、風、陰影,這些曠野的變體,還有幾乎不會融化的“雪”,從未被打破的亙古“寂靜”,還可以加上:孩子,而這是艾基的“老年般-童年”。在艾基所呈現的至為純粹的元素式的世界,只剩下與靜默對等的神-死-愛,和欲言又止的吐露著某種隱秘意義的元素-符號。
艾基基本上不涉及他生活其中的社會現實,因為對他來說,物是實體,而“國家”“大眾”皆為修辭,是詩篇中閃爍其辭的微弱元素,並且深深嵌入或溶解於物性之中。諸如“可能從極深處全民火焰中/亮斑—人民在震顫”(289頁),“趁著還未成為/
溝壑—大嘴—國家
的墓穴之前”(331)。在現代語言習俗裡,一般而言社會是實體,自然-物性只是修辭,艾基則相反,除非作為修辭,他極少提及社會屬性的詞語,有如在苦難的歷史中,詩人創造了一種歡愉式生存情感,將人從歷史的世界轉移至宇宙論式的自然層面,這是大多數人早已喪失的環境、感知和意識。
但艾基又不是人們熟知的自然主義層面上的詩人,他完全不同於葉賽寧,也不同於帕斯捷爾納克。他沒有葉賽寧風俗畫一樣的浪漫村景,也沒有帕斯捷爾納克那樣的抒情主體。艾基的詩更現代,也更原始:一個原住民詩人以土著的活力吸納轉換了最現代的——比如勒內·夏爾及法語詩的——修辭技藝。可以說,艾基以自己的方式改寫了讚美詩,使之轉換為艾基式的聖詩。這部聖詩有著關於自然、心靈與世界之間的神秘編碼。艾基的詩是元素論的:氣(呼吸,風)、水(雪,河流)、木(森林,植物)、土(曠野)。就曠野形象的表層看,這部聖詩由橡樹、樺樹、野薔薇、夾竹桃草、黑麥、雪……構成,艾基詩歌的每一頁上都是曠野,森林和雪。只不過——
在艾基的聖詩裡,荒野越過了自然主義或環境主義的視野,朝向人類內心更古老的信念:荒野會同於聖殿:“會同—統一的——曠野—國(一切越來越完整的——心靈空虛):好像 唯 一 的
神殿
”(《告別神殿》)儘管艾基的修辭已經密佈了“好像”“彷彿”這樣的明喻,但對他來說仍顯不夠,他需要更深的“會同”或將萬物視同的等式,他使用短橫、破折號、冒號來斷開-連結的詞語,實際上是相互“會同”和“統一的”,那就是曠野=國=心靈=神殿,這個表面上跳躍的、斷開的詞語以等式的方式連結是艾基詩歌世界的一種基礎感覺。
換句話說,“曠野”就是“神殿”,這是艾基詩歌的基礎隱喻。由此而來的,存在之物或元素式自然總是發生突然的變容,《曠野:可隨後——毀滅的廟宇》,曠野是一座將毀滅或已毀滅的聖殿-廟宇,但《還有:活的曠野》:“曠野——好像‘有點什麼’好像
‘聖顏’
?”在艾基眼裡,曠野不僅是一座聖殿,還是有跡可循的“聖顏”。就在曠野與神殿的視同隱喻裡,艾基表達著其來有自的關於缺席與在場的思想。他說《曠野——我們不在》:
路的反光越來越近:彷彿歌唱和微笑!
輕盈——儘管滿載——秘密
好像光將它照得越來越亮
上帝——長久的不速之客……——喔差點沒被絆倒——讓它趕到
破敗的小村莊!
僅僅是一條通往小村莊的路,居然承載瞭如此多的秘密。物的存在(此處是“路的反光”)突然轉換為一個事件-聖事,它是艾基聖禮風格詩篇的由來。常常就是這樣,《突然——節日閃爍》:
森林之影愈發澄明
這不——彷彿聖禮之匣
閃著光芒排成一行行
還添加了它
古老讚歌的最後嘆息——
不是詩人在歌唱大自然,彷彿他是一個見證者,一個獲得了恩典的人,被邀請來參與一場聖禮。稍縱即逝的瞬間呈現出一種更高的秩序,這就是詩人感受到的《曠野宿命》:“時間——似乎/像個什麼,比童年更早!——”,“永遠/在不久之前”。曠野終止了時間。世界古老而又年輕。他身臨其間的荒野、森林,有如正在舉行一場隱秘的聖禮,他只是一個受邀的參與者,一個得到撫慰的人。在荒野=聖殿的隱喻(等式)裡,艾基寫到《解憂:曠野》,似乎是曠野在“請你駐足晚禱文”,或聆聽“古老讚歌的最後嘆息”,“彷彿在大教堂裡!——”,這曠野是“永恆地(像風——教堂望不到頭)”。森林是原始的教堂-廟宇-聖殿,這不僅基於詩歌的“好像”,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真理。大教堂或聖殿,只是對森林的原始記憶或起源於對森林的回憶。
《仍舊是——森林》:“歌唱——在森林任何一個地方/它的同一個
神
”。對艾基來說,森林是大教堂,也是同一個神,就像曠野是聖殿也“好像”是聖顏。連《兩棵白樺樹》也“如此:好像神的發音”,輕盈、純淨。《再一次:森林之地》被聆聽:“山楂——歌唱時沉默不語/如沉默的神——在發聲的
詞語
之後”,受邀參與聖禮者需保持敬畏的沉默,“只要一碰——就會:
神
無”。艾基筆下的神,有如自然界的光與影,是永在的瞬息神,與其說它源自一神教,毋寧視為原住民靈性主義世界觀的體現。

作者/來源:blue67sign/adobe/IC photo。
個人的神話詩學
曠野、森林和雪,被會同-視同為廟宇或神靈,或只是神靈的蹤跡與影子,但在艾基神話詩學的意義上,它們有如心靈的“延伸”。艾基寫到《這樣的雪》:
我多想書寫一輩子
“純潔—白色”
——
多想表現出像低語像風明亮的安慰——
渺小一樣美好:
在一篇短文裡,我遺憾地不能呈現艾基詩歌文字形式結構的原貌,那種荒野一樣的空間分佈,只能以壓縮的引文描述一下他的感覺世界。事實上,艾基以連續的話語說出心思的時刻是極少的,但他說“於自己——這已足夠……——”,面對雪野,他看見“生命流逝如空/它的貧乏在發光”,雪野上“些許的榮光——好像
神
/驗過——不—死的愉悅”。在詩人看來,“任何一隻鳥抑或任何一株野草”都是不朽的證據,生命的流逝和死亡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通過了神的驗證和被祈禱改變了的事件,“這不明擺著——此時:恢復最令人信服的祈禱/我低語:‘雪’……”,艾基對雪的描述亦有如參與一場祝福儀式,所有存在物都是明證。
他《愈來愈深地陷入雪》,陷入永恆的寂靜。他說,“我因為貧窮停止喊你/暴風雪降臨之時我們將至臻純潔”(《除了暴風雪還有什麼》)。在艾基的世界裡,似乎《現在永遠只有雪》,詩人“像雪
神
一樣存在”,“雪心靈和光/一切只是在說”,心與物、死與生是一體的,“無
死亡—國度
/噢,還是雪之
神
/心靈雪和光”。在艾基這裡,詞語並置和詞語斷開一樣,都是一個等式,一個比“好像”“彷彿”更確然的肯定,一個萬物相等的泛靈論的等式,它隱隱傳遞出土著人的原始信仰,也是詩人艾基的信仰。
秘密逐漸變得可見,在艾基對自然的描述中,一切事物都發生了變容,曠野是一種充溢的空間,具有恩典意味。這一切源於一個泛靈論的等式,或者說,一個靈性主義的修辭學等式。這種等式普遍存在,如《人們即教堂》標題下只有一句:“心是相互照亮的蠟燭。”雙重的相等構築了一種具有信仰含義的隱喻結構。《花園——憂傷》本身也是一個等式結構的重疊:“彷彿在/我們之間——毫無瓜葛:閃爍!——神父的心”。還有《你——以鮮花之容》出現時所表達的等式:“花—小教堂和花—大教堂,和——
上帝
!——/花—‘我’—
凋謝的
——內心”,一個普遍意義的等式(隱喻)創造了艾基的世界:曠野=聖殿;它的擴充套件式為:荒野=森林=花=神靈=靈魂=永恆=愛=死=……;它的語言表示式為:荒野=符號=沉默。
一種讚歎之情充溢在艾基的詩裡,“噢,
上帝
!多麼/熾熱的
大同
!——”(356)他書寫著一種神話式的宇宙論,一種神話式的元素論和變形記。通常而言,對原住民來說,自然符號背後有著民族的自然神話或原始神話,但艾基的詩不需要這樣的神話。在一種更新了的自然符號裡,隱現著某種個人的神話詩學。他經常寫到的上帝和神,亦更接近一種泛神論,和一種基於泛靈論的人類學。

艾基葬禮。
頌揚貧窮
在艾基的元素式的自然觀和人類學詩學中,連貧窮也得到了頌揚。它們也基於一個淵源深厚的基礎等式:貧窮=純淨。他書寫“明亮的貧窮”(342),他呼喚著“赤貧的兄弟,晨曦中我的天使”(31),他看見“在凍得結結實實的赤貧中/小樹枝一樣……貧窮——在風中”(335),和一切“彷彿窮人的午餐一樣美好”(325)的事物,是因為“貧窮自己發聲/彷彿秋光又好像兒童的臉龐!/它——好像荒野:
上帝啊
”(339),普遍等式創造的語義密佈其間:貧窮,秋光,兒童的臉,最終投射於荒野和一聲呼喚。貧窮如同荒野,但我們不要忘了在艾基這裡,荒野=聖殿。只有在神話學裡,而非社會學意義上,貧窮才得到歌頌並高唱頌歌:“我們有點兒像比苦難還要窮的那部分人/像比一丁點兒也不多的那部分/總算我們完全和睦相處了:
誰一貧如洗
/誰就早點
敞開大門高唱聖誕歌
”(335)。
對這個“熾熱的大同”世界,詩人並不提供論述的理據,他說過這一切對自己“已經足夠”,他提供的是痕跡-符號-沉默。他在《早晨—邊緣》看見:“痕跡(彷彿正是/
巨物
的本質/存在/然後離開)——”這裡似乎有著艾基對現代神學思想的荷爾德林式的迴應:“在可怕的缺 席 之 中/整個—大地純淨和統一”。缺席是不在某個確定的地方,但它卻是“整體”純淨和統一的力量。在艾基看來,《白天——再到傍晚》就是“又一部
千年編年史
(……瞬間的約定……)——
旭日
初升般/絢麗/剛毅”,“約定”沒有被廢棄,不過它不在約櫃裡,而在每個旭日初昇時刻,“永恆——在森林的邊緣——
閃耀
。”
閃耀,閃爍,閃光,是艾基神話詩學中的一個核心觀念,事實上,曠野、森林、雪、路、河流……一切都在“閃爍其詞”。在《閃著光——收割季節》,詩人承認,世界的起源已“不署名”,和“光-基礎的缺席”,但缺席者“像用天空和土壤的容顏!”顯現自身,詩歌似乎是缺席的言語替補,“只有詞語的沉默/閃爍世界的無人稱……”(304)。但“還有荒野在歌唱/橡樹很溫暖——好像它身體裡的感激/跟說話一樣能聽得到”(353)。閃耀、閃爍就是萬物的言說方式,從“輕盈的曠野”到“這彷彿孤獨之心——到處——羞怯的閃爍”(294)。什麼在照亮“曠野的陰影——好似遼闊的苦難!——”,是詩人內心的驚呼和領悟啟示所帶來的身體的戰慄,“戰慄——微風襲來!”“彷彿在看不見的敬意中”“閃亮——”(306)。他《走出溝壑》看見,“左邊——一貧如洗的——故鄉的河——彷彿最小的福音書:噢,閃耀——不為任何人”,一種“荒無人煙的
幸福
之神聖!——”好似對自己已經足夠,卻再也無人分享,這讓他突然發出嘆息:“哦,悲憫……”。在“光-基礎的缺席”的時間裡,萬物的閃耀替代了聖顏,當詩人領受到聖禮,在微末之物中讀到“最小的福音書”,激盪在他心中的是深陷悲憫之中的“荒無人煙的
幸福
之神聖!”
痕跡總是在曠野裡“一閃 而過”,“剩下——閃耀”的符號、戰慄和感激。河流,光,風,故鄉,童年,父輩,逝去的世代,一切都在森林的邊緣閃耀,有如啟示,有如箴言。世界極其輕盈。輕盈是彌散在艾基世界的非物質化的感覺,有如閃耀,有如風,有如雪,漣漪,“不但是天空還有整個大地:閃耀”(308)。萬物閃爍的意義是出現,也是消失,在每一個瞬間。有如呼吸。還有與閃耀相似的“日出的戰慄”(299),萬物的閃耀是有死者才能得到的“戰慄—嘉獎”(193)。詩人在這個時刻所做的,僅僅是戰慄、呼吸、沉默。他說,“是的,呼吸—心靈發射出異彩!”他說:“在那個靜謐裡:早已有://愈發清晰:跟以往一樣:心靈”(206)。當詩人意識到“呼吸—柔情!”就充溢身心,給予“出路/(呼吸的)——//唯有——曠野”(356)。
愉悅式的生存感受
艾基以他獨特的萬物會同或心物會通,恢復了經驗與救贖之間的聯絡,修復了形象與思想的原始關聯。艾基說:“你可以拒絕空曠。
拒絕
陰影—幻象。
還
拒絕——生命。
於是
你會發現——最後的事物,那裡你會重新找到被你廢止的那一切,——那個故鄉——語言。”(203)在萬物相等的泛靈論等式下,事物就是字母-符號-語言。一如《童年》:“滿地都是/調皮孩子們的字母表”,直至,“噢,
直直吹來的、西徐亞的風
”。一切都是基礎元素的變體,是神靈的變容。艾基寫到:
客體?
——越來越多——好像停頓:
那裡新鮮—生產——風!用
世界的聖詩!——
在艾基詩中,一個神話詩學的世界“跟它的反覆吟唱一起——/呈現(……)”(193)。詩人需要客體,因為形象就是可見的觀-念。而自然元素之間的“會同”或萬物相互押韻,構建了艾基獨創的“歌謠-共和國”(214)或神話詩學。
必須沉浸在無意識狀態才能讀進、聆聽進艾基的詩,“用心靈感知/在自己業已生疏的心中”(192)物是符號-語言-無意識。當物僅是我們意識載體的時候,當我們說“樹人”“建樹”“樹立”的時候,“您歌頌的——業已凝固”(216),當物沉入無意識的時候,事物才言說-沉默。
譯者駱家將艾基的詩描述為“沉默詩學”,這是嵌入獨特話語中的沉默,“彷彿能融化思想”的事物和“點燃我—
思想
”(144)的存在擁有同一種根源。這是一種從無意識向意識維度延伸的語言,就像從黑夜朝向黎明,但卻在語義晨光熹微的中途停頓。停頓在這一刻是必要的,言說的省略是必要的,以便從論說轉向歌唱-語言的歌謠。因此艾基詩歌文字顯現為語義鏈的斷裂和語義的不飽和,句式斷裂為詞語的不規範分佈,詞語分裂為字元,還有頻繁的間隔、斷層、錯行,這是一種讓沉默進入語言-語義的符號形式。它意味著真理-信仰的邏輯環節斷裂了,而信念的節點卻都被一一提示了。或許,碎片式的元素-話語,一直在尋找自身的總體性-宇宙論。此前,我們曾在狄金森那裡看到過對“……”“—”“——”的語義化使用,艾基更極端地使用短槓、長橫、破折號、括號、省略號……或許這些符號的語義化,更接近某種原始符號,更趨向歌唱與呼吸中的停頓和沉默。每個詞都像是一聲嘆息,一種被打斷的可能性。或許這樣的修辭結構與“基礎的缺席”及“痕跡”的“閃耀”這一神話學的感知有關。有如無際的楚瓦什曠野上散落著原始神話經驗-記憶的片段。
艾基的讚美詩,非關具體的宗教,他的讚美詩處理的是文化轉型時期如何保留人類心中的讚美、虔敬之情的一種詩歌,在接受任何具體的真理之前的讚美詩。艾基在《駐足之頌》中說:“我說——讚美‘你’”,只是“一切——世界的相互自我呼應/聲音的洗滌!——”。詩人書寫的不是自我之歌,而是“你的秘密——於我——好像歌唱!——”,“做一個——宇宙的孩子”而歌唱(329),他的詩歌是迴應伴和那“自古以來—年輕的
聲音
”,他認同“那個聲音跟
神
諭一樣”,他加入一種和聲,“‘我’——聲音聯合起來!——//從森林裡歌唱的地方組成的大教堂/全都是神在歌唱!”(146)
閱讀艾基的詩帶給我們一種久違的愉悅式的生存感受,相對於歷史的是自然,相對於理性主義的是詩的靈性主義。靈性主義之於當代文化,似乎唯有詩歌才是合法的表達方式,或見容於當下世界。然而,詩歌的靈性主義是一種剩餘的宗教元素、殘餘的信念,還是一種孕育著未知之物的語言?從荷爾德林到艾基,什麼構成了他們在觀念史上的意義?
是否可以說,艾基的詩,他的“歌謠共和國”是宗教內在化的一個階段,是信仰進入無意識層面的一種表現?“一切都結束/卻仍在繼續”(305),宗教內心化、內在化需要一個形式,一種個人的儀式,一種語言上的禮儀或聖禮:這就是詩歌。艾基的這樣一種聖禮風格的詩尤為如此。靈性主義或靈性體驗,並非自我聖化的意圖,儘管不排除在內心尚未抵達這種理解的人們那裡,詩歌的靈性主義未能擺脫自我聖化的傾向,但在艾基,或許我們還可以想到雅姆、聖-瓊·佩斯這樣一些保持著頌歌精神的人,詩歌是一種“在虔敬的情感或讚美的心境中說話”的可能性。
它與教會制度層面上的宗教信仰沒有關聯,作為制度層面的宗教已經歷史化,或許聖禮風格的詩篇是歷史化過程之後的一個更微妙的階段,或者,更微妙的精神層次。艾基不是先知,他只是一個感知者。他的靈魂中有著屬於過去信仰的元素,也有著指向未知的信仰元素。
艾基說,《再一次:從夢開始》——
夢怎樣發聲?
嘈雜不清的思想
透過不曾有過的
類似“噢—是的—已經—在準備”的言語……
作者/耿佔春
編輯/張進 王青